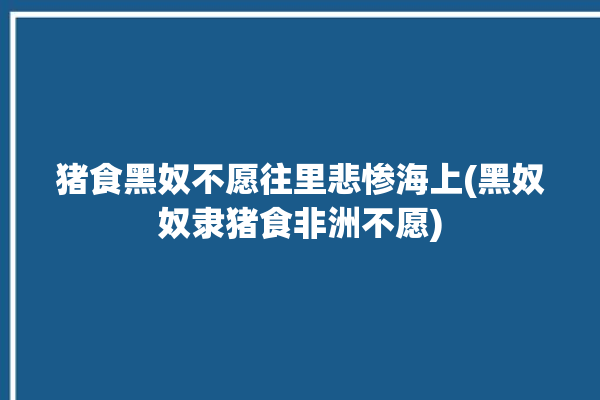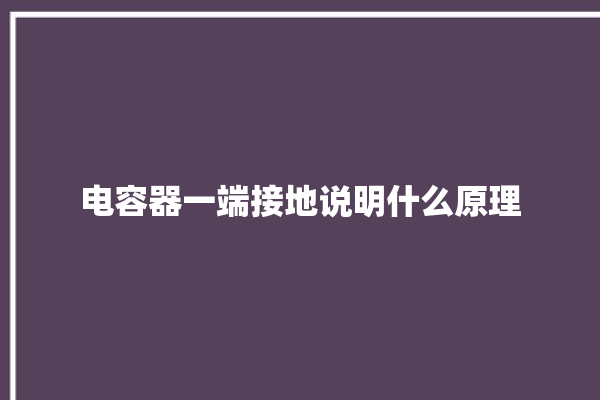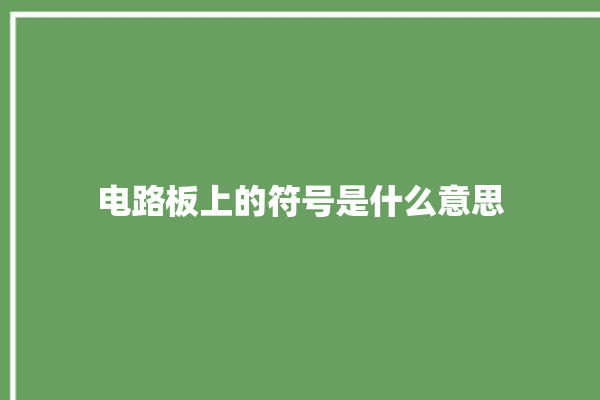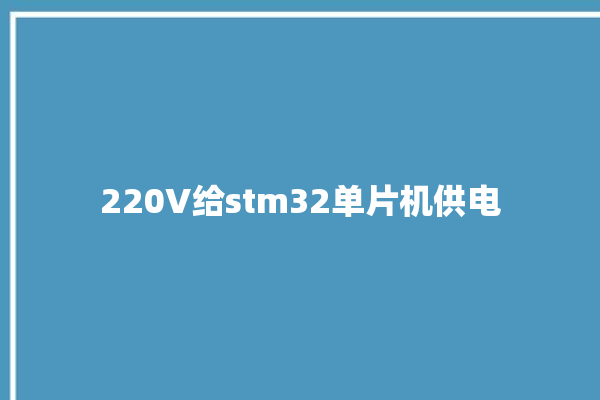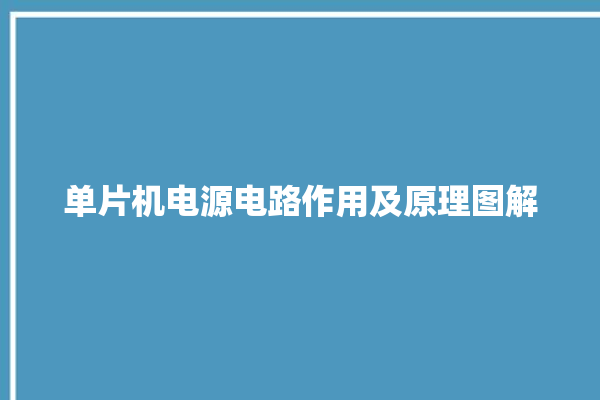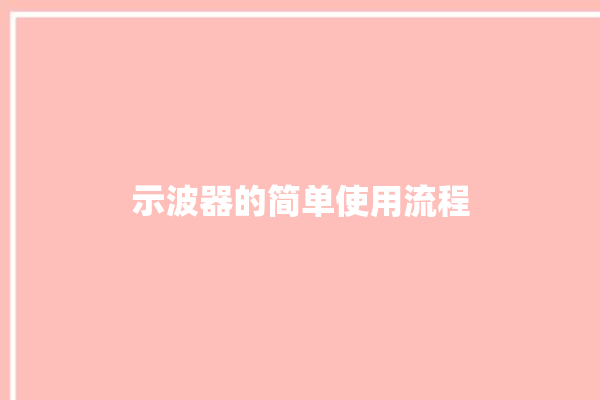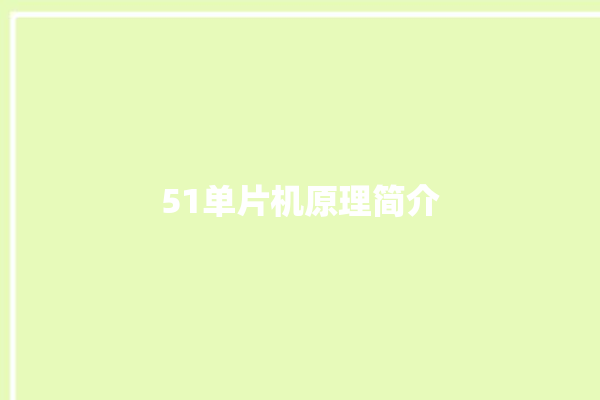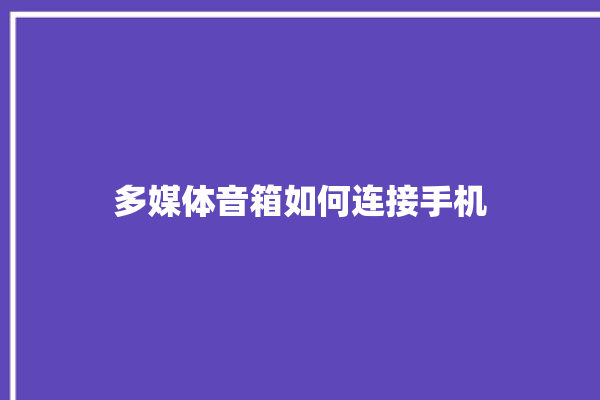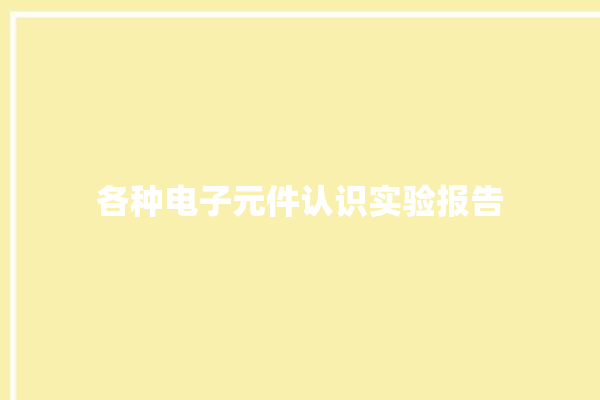从今日的塞内加尔(Senegal)到安哥拉(Angola)之间约五千六百公里处;其中,又以昔日称作黄金海岸(Gold Coast,今日的加纳)、奴隶海岸(Slave Coast,包括今日的加纳东部、多哥(Togo)、贝宁(Benin)、阿尔及利亚)、喀麦隆(Cameroon)等地为最。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始作俑者的葡萄牙几乎垄断整个奴隶贸易市场。1640年代,英国、法国、荷兰开始分夺势力。到了十八世纪,英国人成为龙头老大,并一直持续到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毫无疑问,如此庞杂的贸易体制不是欧洲人独自形成的。欧洲人枪炮再强,也没本事上山入穴掳走成百上千万非洲人。最初,他们也企图攻城掠人,终不敌彪躯魁伟的非洲人;也证实了唯一的途径,是携手合作。未久,贪婪的欧洲人和非洲本地贵族建立起一个非常系统化的高效率贸易方式,确保各方都能分一杯羹。在非洲当地贵族的要求下,欧洲人只能担任黑奴的运送者,绝对禁止介入非洲政治,不能到非洲贵族的土地上抢掠人口,非洲贵族会定期捕获一些黑人和欧洲人进行贸易。黄金海岸沿海的城堡、港口,是最火热的欧洲商人与非洲贵族交易的地方。高大阔气的海岸角城堡,是当时英国人在西非的总督官署,也是奴隶贸易全盛时期的贸易中心。欧洲人总共在西非海岸建了四十五座城堡,其中三十二座位于加纳,当时最权威的欧洲贸易商: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葡萄牙人,几乎都在加纳拥有奴隶城堡。在这里,欧洲商人获得现成的奴隶,非洲贵族则拿走珍贵的货品,买者卖者讨价还价。当时最受非洲贵族上层欢迎的货品包括枪枝弹药、烈酒、欧洲衣物、东方器皿、铁质刀具、钱币、饰品、盐巴以及纸张等等。面对琳琅满目的舶来商品、诱人垂涎的肥硕利益,不少非洲统治者依然试图阻止这场贸易。早在1526年时,原与葡萄牙人关系良好的刚果阿方索(Afonso)王,向葡萄牙国王投诉葡籍奴隶贩子绑架他的子民。1630年,恩东加(Ndongo)的尼京哈.曼班蒂(Njingha Mbandi)女王曾将欧洲人赶出领土。1720年,达荷美(Dahomey)的托多(Agaja Trudo)王不仅反对贸易,还动兵攻打欧洲人的城堡。其他非洲统治者诸如刚果的金帕.维塔(Donna Beatriz Kimpa Vita)和现今塞内加尔北部的阿布杜.卡迪尔(Abd al-Qadir),都曾力抗欧洲人的贸易侵略。只是这些力量,终究未能力挽狂澜。非洲大陆上的人民像泄洪般的湍水,一去不复返地,流向另一方。在海岸角城堡的“不归门”(Door of No Return)旁,有记者遇到从美国去“寻根”的杰克逊:“我当然知道,要推探我的祖先到底来自非洲的什么地方?他们曾被关在哪座城堡?他们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吃着什么样的食物?唱着什么样的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踏上这片大陆,结果,寻到的只是一种不能承受的茫然。”曾经,他的祖先可能也从“不归门”,穿过长长地道,走向某一艘运奴船,从此再没有见到故乡。当时来自各方的奴隶,几经易手、几度更名,许多可以验明身份的证据都误乱缺散了;当时被掳被卖的奴隶多目不识丁,欧洲的官商记录则难免乖违实情,许多事迹细节也早已不可考。“登船之路,是惊悸可怖的。只听见枷锁撞击的嘎嘎声、长鞭打在身上的啪啪声、呻吟与哭号……”被非洲奴隶贩子以一件衣、一枝枪、几颗子弹卖给欧洲商人的加纳奴隶鄂图巴·古瓜诺(Ottobah Cugoano)留下的回忆录,为运奴船修得光鲜的门、刷得粉白的墙,添抹了些许讽刺的注释。如今,如果去加纳游玩,参观海角地区,推开“不归门”,城堡外,会有一派祥和的大西洋海岸风光,风平浪静,谁也想不到从这里出海的运奴船在大西洋上经历的几百年惊涛骇浪。当地的渔民有说有笑晾晒渔网,讲着黄色段子;妇女头顶杂货边走边聊,说着各家的家长里短;景点小摊贩在遮阳伞下打盹,面前摆着整排奴隶船木雕纪念品。那里会有很多在午后日光下踢球、玩沙、追逐海浪的孩子,他们在看到观光客即手舞足蹈地齐声大喊:“Obroni
Obroni
Akwaaba
Akwaaba
”(外国人
外国人
欢迎
欢迎
),以求富裕的外国人能赐予他们一点零花钱。尽管有着如此沉痛的过往,加纳人对外国人的热情友善有时却铺天盖地得叫外来人相当错愕。据说,加纳人只会对白种人(包括东亚人)热情,加纳人绝不会对迦纳人,或任何黑人这么好。如此魔幻现实主义,反复上演在和加纳有相同经历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