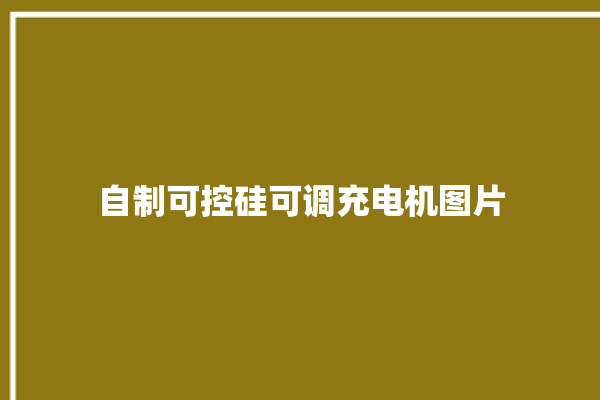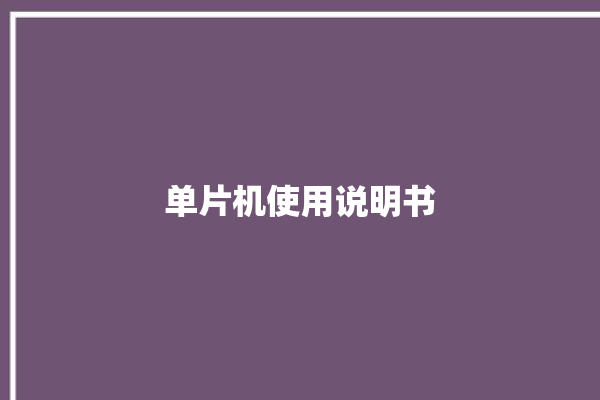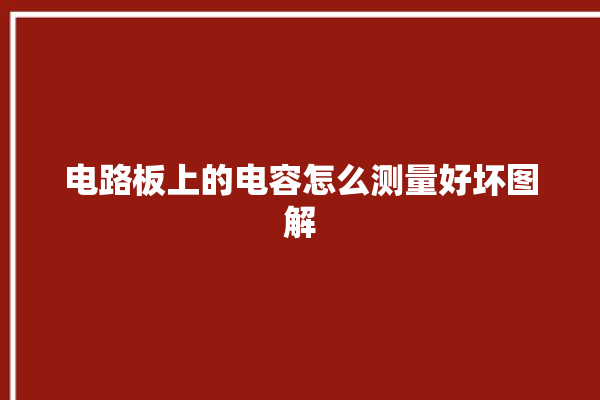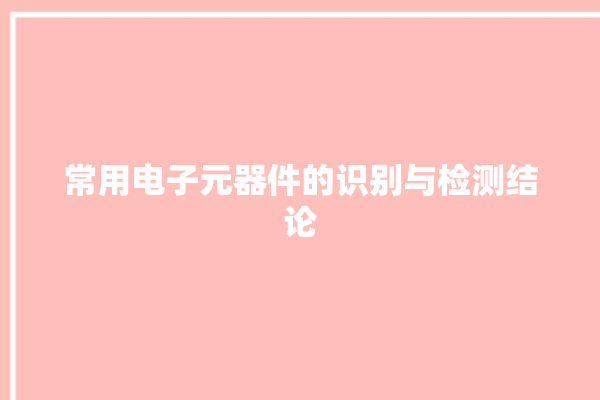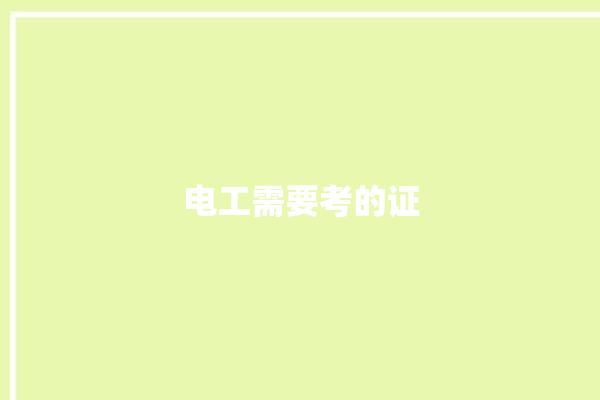但是,很遗憾,尽管这个玩意能解当下燃眉之急,却无法推广。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个设计或许更像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辅助治疗手段。无论如何,随着这种依赖和其相关比喻意象的不断循环,包括我们发展的对瘾症的治疗,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又回到了原点。无聊是由环境引起的;个体以压力的形式感知无聊;这种压力必须得到释放;上瘾行为可能是缓解方式的一种循环。最糟糕的是,这是我们随着进化与生俱来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在第一时间就限制无聊的出现。不过,但让我们更清楚地指出其中的社会和政治假设。新奇感本身也许能部分地解释我们与生俱来的属性,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此外,无聊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往往特别是在有大量刺激和毫不费力的短期欲望满足的情况下。无聊是症状,而不是疾病。如果不这样认为,就会再次成为新自由主义对自我描述的牺牲品。毫无疑问,对于这些观点的讨论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只要记住,在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有关这些努力的政治争论背后,隐藏着全面自主的自我问题,对此我们必须继续报以怀疑的目光。这一点与卡夫卡殊途同归,但并非巧合。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讨论卡夫卡式幽默的独特之处时指出,他很难向他的美国学生传达这些看似黑暗的作品的滑稽之处。华莱士说,问题在于,卡夫卡式幽默并不符合学生们已经掌握的所有明显的类别。这不是挖苦,不是反讽,不是胡闹,也不是故作伤感。事实上,卡夫卡式幽默是一种深奥而令人生畏的东西,但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因为它具有人性。欣赏卡夫卡的作品就如透过一扇黑暗的玻璃,看见了自己。约瑟夫·K(Josef K)被控犯有他和我们都不了解的罪行,并帮助那些倒霉的刽子手弄明白了如何挥刀结束他的生命。站在看似被锁上的天堂之门前的那个男人,后来变得神志不清,开始和他饱受折磨的外衣领子上的跳蚤交谈(而门一直是开着的)。华莱士认为,这里的幽默不是你用领会笑话的方式就能“领会”的。他的学生感到困惑,因为“我们一直都教他们把幽默看作是你能领会的东西——就像我们一直教他们自我就是你与生俱来的特质一样”。因此,难怪学生无法欣赏那个带有卡夫卡精髓的笑话,那是一种可笑又可悲的讽刺:“痛苦挣扎着建立人性自我,结果这种痛苦挣扎就此根植在自我的人性中,不可分割。那么,我们无尽且无望的归途,其实就是我们的归宿。”完全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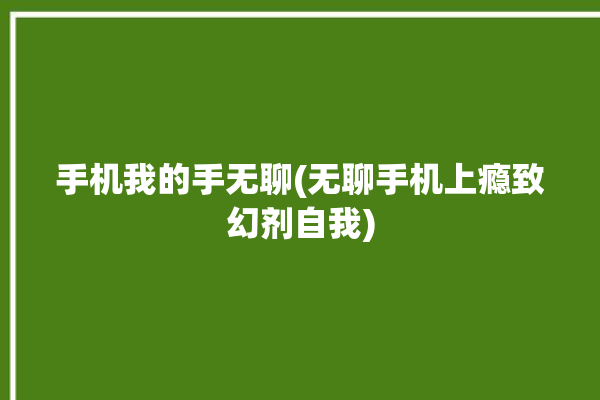
如果我们永远处于T.S.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Burnt Norton)中生动描述的状态——“既不充实也不空虚。只有一抹微光/ 闪烁在一张张憔而饱经风霜的面孔上/ 心烦意乱不得安宁/ 充满幻想和空洞的意义。”——我们就不会正视这一事实,从而根本意识不到实现自我的复杂性,更不用想着轻而易举地将自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前提假设了。当我们专注于消除无聊,或将无聊转化为创造力或进一步的消费时,我们纯粹在(可能是无限期地)推迟与自我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对自我至关重要。无尽又无望的旅程往往都是无聊的,然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踏上的旅程。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解剖无聊》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