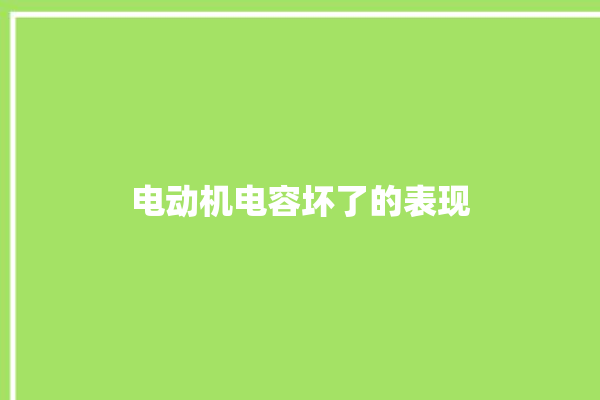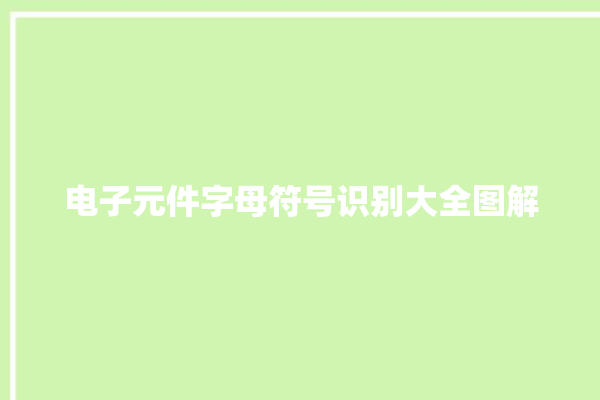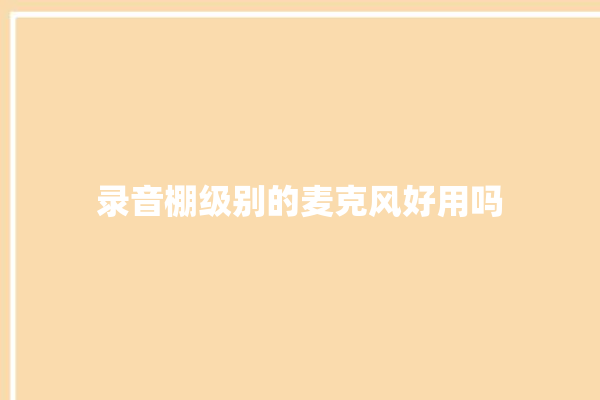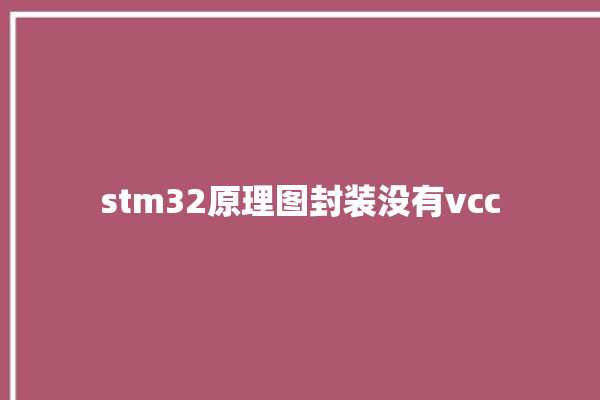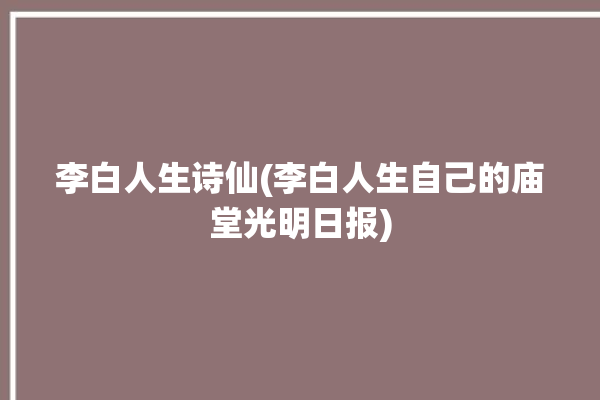
这部新戏文化含量高,文学性强,又能雅俗共赏。它以当代人的诗性理想,将李白与长安相关的一些传说故事及诗词,熔铸进古丝路文明互鉴的宏大主题中,在戏曲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之间找了很好的融通渠道。其间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和阐释的话题。这可能就是一个戏有深度的表现吧。这是李白第一次作为大戏主角登上秦腔舞台。剧作者将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置于与其个性相异相悖的宏大叙事架构中来展开,更是给自己出了难题。现在所以能够较为准确、深刻地写出李白这个人物,我感到主要有赖于编导致力表达了诗人精神世界的复调色彩和多元化倾向。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有的更倾向于儒,例如杜甫;有的则更倾向于道,例如李白。但他们的精神性格绝不只是单色的,而是复调的,有着一种雕塑般的立体感。他们各有自己精神的主调,又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复调结构。戏中的李白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的李白、传说中的李白,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诗酒情怀。他好诗,才溢古今,好酒,醉酿性情,在诗酒中将自己的精神品格和现实感受推向极致,提升到审美境界。豪放和才情成为这个人物众所周知的气质。但其实,李白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嗜酒的文人,却又不甘于浸泡在诗酒人生中枉度岁月。他对自己的才能相当自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对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渴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对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充满着自信。这构成了另一个李白。从这个角度,即人生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李白的功名之欲、入世之心,那种积极的进取意识,与儒家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自孔孟以来,儒者奉行的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李白其实也是这样。他希望自己能够辅佐帝王平治天下,建功立业。可以看出,李白人生价值的核心乃是入世有为的“儒士精神”。这儒志同时又兼具着道心、侠骨、仙风的多重色彩。儒侠仙合一、狂狷逸聚身的李白,在长安的三年中,试探着由山林走进庙堂,开始了他由诗酒人生向庙堂人生的转化——他以这样“另一个李白”的形象出现,实在是一次精彩亮相。李白这种多维的、复调的性格,在剧中是逐层深入塑造出来的。一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玄宗、贵妃、李白、贺知章、薛仁以及群臣之间的诗酒心仪,诗酒相惜。李白以他的才华得到了贺知章、王维的推荐,而他又因诗情文才赏识了新科进士薛仁。上朝后,与唐玄宗、杨贵妃更是一见倾心。这是一种惺惺惜惺惺的诗酒人生。玄宗、贵妃能乐善舞,掌管天下却不乏诗性情怀。他们构成了一种同向的互文关系。随着宫闱乐女花燕的出现,事情开始起变化。两个青梅竹马相爱的年轻人活生生被宫廷分离,激荡起李白的侠义精神,喷薄于诗酒人生之上。他挺身而出要管这个事,而且一管到底。后来,诗人发现了薛仁、花燕爱情背后更大的社会内容,就是边关禁止史籍兵书外流,妨碍文明互鉴的问题。事关丝路文化经济交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李白,更有着西域的人生经历,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与那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于国于民于心,都使他义无反顾地由侠骨柔肠,突进到治国理政、为社稷担当的层面,和奸佞之臣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帮助朝廷翻译、草拟大唐与康居国的往来公文。他强劲地介入社会,显示出内圣而外王的儒家人格追求,为古丝路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这在古代诗人和文士中是罕见的。剧作者抓住这条线作了突出的处理,便超越了具体题材,而在历史文化和民心相通层面,融接了古今,一部古典剧、一个古典名士也便有了当代意义和感情温度。在李白人格精神这第二个阶段,诗人与玄宗的互文关系,由同向转化为对立再回归同向。他看到了奸臣当道、忠臣无为、朝廷受蒙蔽的一面。他的酒醒了,义无反顾、也不屑一顾地挺身而出。他进入了儒家入世有为的境界,由诗酒人生转向庙堂人生。复调人格中的儒志,便这样得到了有力的突显。最后,当朝廷采纳了李白、贺知章的建议,解除了边关禁书的不当禁令,丝路文化交流重又畅通,玄宗夸赞、赏赐了李白,也给薛仁封了官。我们的谪仙人似乎即将开始他辅佐圣上的新的人生了。这时,诗人却出人意料地提出要谢别圣上,归隐山林,去浪迹天涯。剧情出现了一个陡转。这转折看似意外,实在意中,是李白性格的必然,也是他人格境界新的升华。与朝廷的交集中,他虽然在维护薛、花爱情和力主丝路文明交流上有所实现,却也有着更大的失落和更深的失望——那是对于皇权的失望,是自己乃至庙堂文士普遍的失落。他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了诗酒人生乃至雅士、文化,在皇权眼中只不过是酒后茶余的帮闲。他不屑于在朝廷仰人鼻息,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他希望与圣上成为文朋诗友,甚至于希望像诸葛亮、吕尚、谢安那样成为庙堂之上的先生,立功立德立言以报效社稷。当知道这一切毫无可能,跌入深深失望之中的诗人,只能挂冠而去,在道骨仙风中去追求生命本体的真实了。三年长安行,终于回归真性情。李白由庙堂人生最终又转向了山林人生,这是李白人格的一次高层次回归。儒志是对仙风的一次提升,道骨又是对儒志的二度超越。李白在剧中的这一精神历程,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在他们狂狷的人生形态里,常常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大志。即便退而独善其身,也依然眷顾着社稷生民。李白就在他的游仙诗中不止一次写到对现世的眷恋如何惊醒了自己的游仙之梦。他虽升空而去,却忍不住俯瞰大地的凄凉:豺狼横行、血流遍野而心忧如焚(《古风》第十九首),也写到他在仙境对尘世帝王轻蔑的一瞥(《来日大难》),所以我有了观剧的第三个感觉:这真是“更加李白”
(作者:肖云儒,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