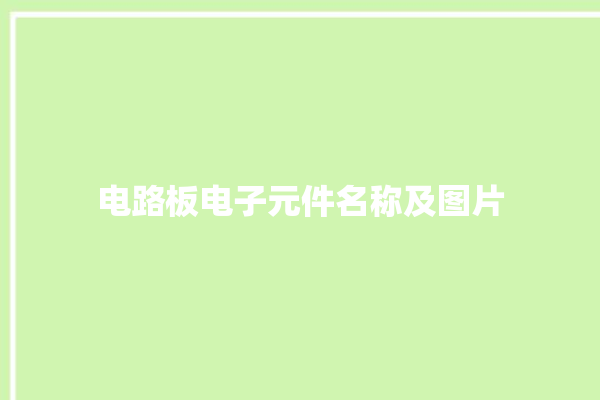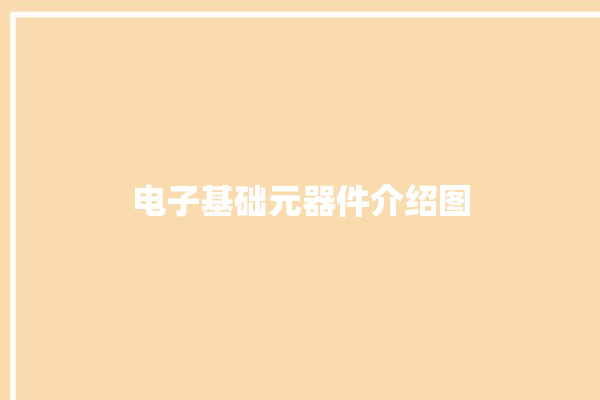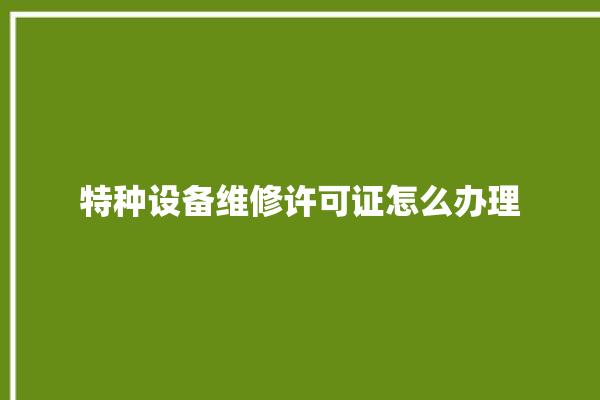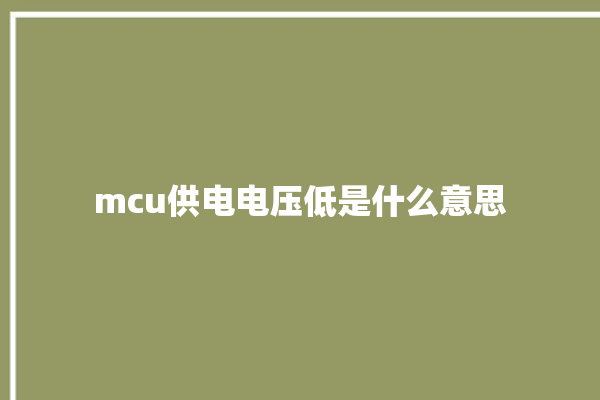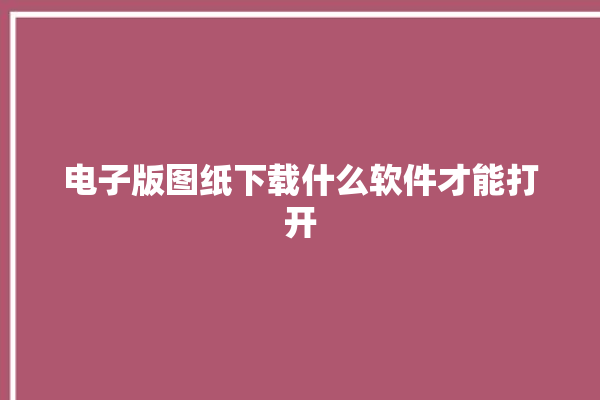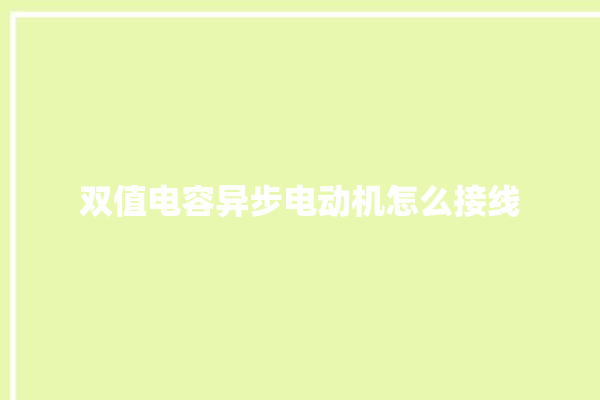”没想到,沈从文听完这句话后,抱着那个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说,就是不停地哭。后来,还是张兆和走过来,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抚摸又安慰,他才安静下来。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的一个部属立的,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黄苗子看了后,称赞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是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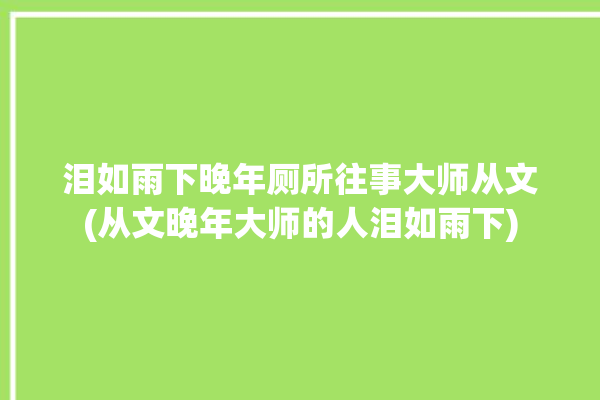
后来,黄永玉把这张拓片拿给沈从文看,“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
是不是,你好神气
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1987年7月,瑞典作家汉森和汉学家倪尔思对沈从文进行了访问,汉森给沈从文带来了一份复印件,是1949年瑞典杂志上刊登的沈从文的《萧萧》。上面有瑞典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边城》的广告,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着话说:“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说完这句话,沈从文忽然流泪了。有人觉得这样的沈从文颠覆了他们对大师的认知,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怎么还那么爱哭泣,那么矫情呢?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大师的哭泣,每一滴,都是情怀,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老人的眼泪。我想起我的奶奶,八十多岁的时候,她特别爱哭,像一个孩子一样。有多年不见的亲戚来了,她会哭,亲人走的时候,她就用手拽着他们不让走,说,多玩两天吧
下一次你们再来,就看不到我了
说完牵起衣袖,一点一点地擦起眼泪。后来奶奶不在了。我奶奶的侄子,也老了。他年少的时候意气风发,一个人闯下一片天,吃了不少苦,最终培养出来五个优秀的子女,富甲一方。但到了晚年,也开始变得像我奶奶一样,多愁善感。每一次我们去看他,他都高兴,每一次我们走,他都抹眼泪,弄得我们都心里酸酸的。去日无多,他站在暮年的夕阳里,朝我们一遍遍地挥手。每一次哭泣,都是老人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眷恋,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哀伤。一代代的人,哭着老去了。再回头的时候,青山依旧在,夕阳依旧红,但那个身影真的就永远消失了。有没有一天,我们垂垂老矣茕茕孑立,对着来看望我的子孙挥泪如雨。然后,去我们终究要去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