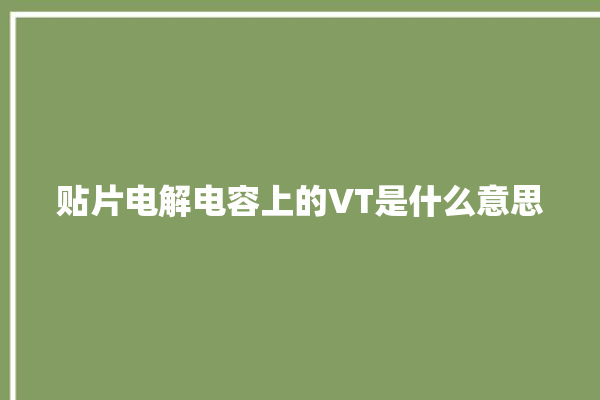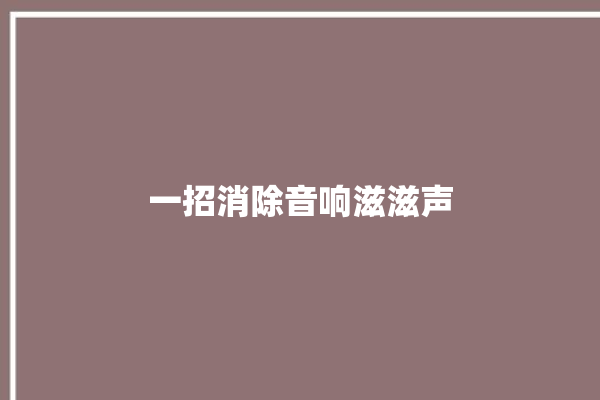上世纪五十年代能挣89块的工资,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那时,我家住在城隍庙后街的14号院子东耳房。父亲因为工作努力,年年都是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后来又成了大同市的劳动模范。我家后墙挂满了父亲的各种奖状。▲陈民义的父亲父亲40多岁时积劳成疾生病了,住到原来五一菜场旁边的交通局医院,那时的医院医疗条件很差。交通局医院三排平房,医疗设备也就能照个X光,治疗也就是天天输液。医生安顿我妈,隔一天搞只老母鸡给熬点鸡汤补补。住院的医药费单位全出了,不用自己掏一分钱。父亲住院的时候,母亲一直守在身旁,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去看望。每当我去的时候,父亲早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白皮焙子,里面夹着两片猪头肉,用纸包着放在床头柜里,就等着我去。有时候,他还带着我出去到医院旁边的五一菜场,给我买一块海绵糖吃。▲小时候的陈民义父亲出院后不能胜任原来的工作,单位照顾他身体,就让他到站东北辰那儿有个东风社的草料场看场子去了,在那儿一边养病一边工作。不过,他还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起早贪黑赶车,特别是春秋季节的时候还常趟水过河,落下了病根,有一天心脏病突发,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才44岁。父亲去世后,东风社的马掌柜(我们叫马叔)领着母亲去结算。母亲不识字,又是家庭妇女,单位的事情啥也不懂。马叔领着跑前跑后办理各种手续,最后结算了780块钱,10块10块的一大摞,在当时那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母亲把这笔钱为我存着,不论有任何困难都不动用。母亲年轻守寡,又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艰难。有人给我母亲介绍了一门亲事,姓刘。母亲带着我们就嫁了过去。母亲嫁人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不论嫁谁,我儿子不改姓,只姓原来的陈姓;第二,我丈夫留下的钱不能花,那是给我儿子留着的。我家原来的东西,洋箱、柜子、水瓮,所有的家什都可以归你,但这钱一分都不能动。”▲当年陈民义母亲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后来我们在刘姓这家并没有待多长时间,大约就是半年多,母亲就带着我们离开了这户人家。再后来我姐姐早早找了婆家,19岁时就出聘了。母亲带着我还在县楼南的姐姐家寄居了小一年时间。姐姐家住一间半小房,我和母亲、姐姐、姐夫就挤在那低矮的房子里。父亲去世后,我家没有了生活来源,也不能光靠着姐姐姐夫生活。原本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也不得不开始找工作,正好院人给母亲介绍了一份在木业社的工作。在木业社工作的十几个女工里,母亲是最瘦弱的,厂里的工人知道我家的境遇后都特别地关照,尽量给我母亲派一些较轻的活计。工友们关照归关照,我母亲自尊心极强,啥事也不愿落在大家的后面。那时她们社里要去安益街木材厂拉木材,她也跟着去装卸,回来的时候一帮人就都挤坐在高高的木材垛上。木工活计极其费手,当时人们压根没有劳动保护观念,即便是发一副手套也舍不得戴,留着攒的多了卖钱补贴生活。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手永远是粗糙的,十指上缠着一层一层的白胶布。那胶布上由于沾着胶水的缘故,变得黑不溜秋,无法洗净。木业社一个星期给各家分一袋烧火柴,每次都是我推着车子去木业社拿回家烧火。▲陈民义和三墩村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后来母亲又经人介绍认识姓杨的继父,我家才搬到七佛寺。从城隍庙后街到七佛寺,从城北到城南,短短的三四公里我们整整走了12年。过去孟母三迁是为了孟子的学习,如今母亲带着我们“迁徙”纯粹是为了生活。到七佛寺后,我和母亲的生活在继父的照顾下才算慢慢有了模样,才算慢慢稳定了下来。稳定是稳定了,但当时的生活依然十分窘迫。在七佛寺,我们依然住着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南房,我、母亲、继父和继父带来的姐姐都挤在一起。炕小睡不下,继父每天在锅台边上搭上一块木板才能躺下。我上高中的第3天,刘光锐老师到我家家访,看见了我家居住的窘迫,回学校特意为我申请了住校。我是当年一中唯一家在市里但又住校的学生。刘老师又帮我申请到当时最高的助学金12块。我除了交8块伙食费,还能剩4块。我住校了,我妈怕我吃不好,营养跟不上,每个星期都用饭盒给我拿半斤猪头肉去学校看我。▲陈民义在大同城墙上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每想起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生活,总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我也常常感叹,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要是母亲活到今天,该有多幸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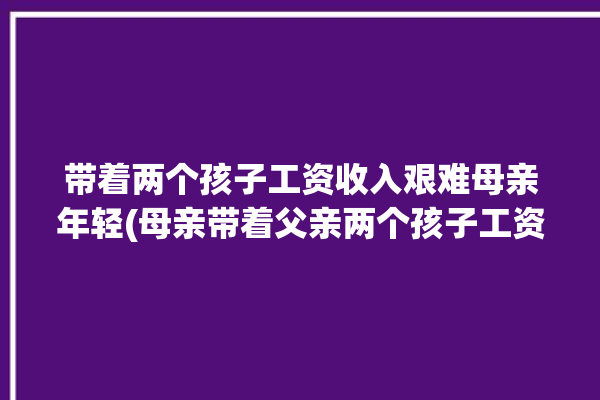
陈民义现在是长城的志愿者陈雁秋大同资深摄影人陈雁秋先生拍摄了很多大同古城老照片,作为老大同人,他为这座老城拍下很多珍贵的影像,为我们记录下老街古巷的点点滴滴。同时,他也正在收集整理老照片里大同人的故事。上面这个地方您熟悉吗?如果您与这个地方也有故事,期待您分享出来,请在留言区写下您的故事,或投稿给我们。投稿邮箱:hy1200@126.com策划 | 贺 英责编 | 周建新审核 | 邓 琳监制 | 杨 刚